译文及注释
译文
梁元帝曾说,王粲在荆州为刘表效命时作了数十篇文章,后来荆州被攻破,王粲便将自己的文章全部烧毁,仅留了一篇。当时的文人名士看到后都称赞写得好,但是遗憾不能看到全貌。后来都城江陵被西魏宇文泰带兵攻陷,梁元帝也将自己所藏的书全部焚毁,说:文王、武王的治国修身之道,到今夜完全消失了。为什么与荆州沦陷时焚毁书籍的事情如出一辙啊。于是作诗表示感慨。
王粲和梁元帝十分爱惜自己收藏的书籍,但在自己所在的城池被攻陷以后,却一把火烧掉了自己所有的珍藏。
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未赶尽杀绝,才能使那些残留的诗文保存到今天。
注释
金楼子:书名。梁元帝为湘东王时自号金楼子,因以名书。《金楼子》是梁元帝从青年时代起就亲自动手搜集材料逐年撰写而成的。梁元帝,即萧绎(508—554),初封湘东都王,承圣元年(552)登基,称梁元帝。梁元帝一生博览群书,儒释道兼通,而且还完成了大量学术著作,所以《梁书·元帝本纪》称赞他:“既长好学,博综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史称其藏书十四万卷,于江陵城破时自己烧毁,并用宝剑狂砍竹柱,仰天长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王仲宣: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三国时曹魏大臣、文学家。其祖为汉朝三公,与李膺齐名。早年王粲曾得到蔡邕的赏识,汉末动乱中,避乱至荆州(今湖北襄樊)依附刘表。刘表以王粲其人貌不副其名而且躯体羸弱不甚见重。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归降于曹操。曹操辟王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王粲文学成就颇高,尤以诗赋见长,与刘桢、孔融等合称“建安七子”,与曹植并称为“曹王”。有《王侍中集》。
咸:都,全。
“见虎一毛”二句:以虎身花纹的斑驳多彩比喻王粲文章的成就,非一文而可知。语出《周易·革卦》,其“象辞”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疏曰:“文章之美,焕然可观,有似虎变,其文彪炳。”
西魏:北魏永熙三年(534),鲜卑族宇文氏所建立的北魏政权分裂为东西两部,西魏都长安,至恭帝四年(557)为北周所取代。
尽焚其书:《南史》卷八记载,梁元帝酷爱读书,平时手不释卷,无论冬夏。当西魏攻江陵,元帝知城不可守,准备投降,“乃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
牙签:象牙制作的图书标签,写上书名,垂于卷轴式书籍的一端,以便查找。这里代指书。红绡:红绡制作的书套。绡,生丝织品。
祖龙:指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壁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秦始皇死于此年。裴骃《集解》引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像。谓始皇也。”因为其曾焚书,故将其与焚书事相关联。▲
创作背景
这是李煜读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后题写其书后的一首诗。据诗前小序,李煜《金楼子》后,对读《金楼子》所述的焚书事件深有感慨,便作了这首诗。
这首诗见于宋代无名氏的《枫窗小牍》,云:“余尝见内库书《金楼子》有李后主手题曰:梁元帝谓王仲宣……”可见,《枫窗小牍》作者曾在皇家书库见过梁元帝的《金楼子》,而此书正是赵匡胤从南唐那里掠夺来的,显然曾为李煜所有。据此,此诗当作于李煜入宋之前,也可能是即位之前所作。
赏析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李煜(937年8月15日―978年8月13日),南唐元宗(即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莲峰居士,汉族,生于金陵(今江苏南京),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铜山区),南唐最后一位国君。李煜精书法、工绘画、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传统,又受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其亡国后词作更是题材广阔,含意深沉,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
 李煜
李煜 陈曾寿
陈曾寿 陈子龙
陈子龙 萨都剌
萨都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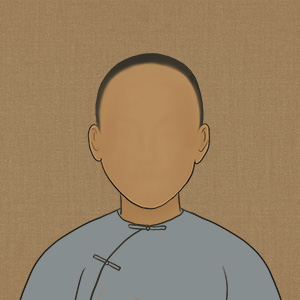 胡秉正
胡秉正 韩愈
韩愈 欧阳修
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