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
这首诗作于万岁通天元年(697)作者从建安王武攸宜东征契丹时。借一位游侠的怀才不遇,为之鸣不平,来表现自己壮志未酬的“兴寄”,并对统治者埋没人才予以讽谕。
赏析
此诗的开头两句,以苍劲古朴的笔触勾勒时、空背景,渲染出悲凉的气氛: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深秋时的渤海要塞,凛冽的北风吹刮着浩瀚大海岸边的树木,呈现出一片凋零、萧飒的景象。背景画面苍凉,但气势飞动,“海树”以“海”迭加于“树”,就使得这个意象雄浑而有风骨。动词“吹”,副词“已”,亦用得骨劲气遒。
以下引出诗的主人公: “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亭堠乃边塞哨所;“楼”即亭上的戍楼。“明月楼”,既具体点明此时乃深秋月夜,又使形象充满“哀”怨,启人联想到“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曹植《七哀)》的境界。曹植为“建安作者”之冠冕,钟嵘誉之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诗品》卷上)。此诗三、四句学习《七哀》但并不照搬。《七哀》写女子,此写游侠; 子建尚有“柔情丽质” (钟惺《古诗归》),子昂却刚健质朴。
诗接下来转入主人公的自述,是全诗的主体部分。前面不明说楼上戍卒到底是“谁家子”,既引逗读者的遐思,又可把“哀哀”的情调渲染足,有“盘马弯弓惜不发”的顿挫之致。在此基础上,才如《七哀》 “借问叹者谁?自云宕子妻”的句式一样,挑明主人公的明确身份与经历: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战国时燕国之地,汉以后置为幽州,连称为“幽燕”,属今河北北部与辽宁西部一带。古时男子二十岁结发而冠,表示成人。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尚武崇勇,故“幽燕客”三字足以表明此人乃一侠士,他胸怀大志,刚一成年就离家远游,以求建功立业。不是恋巢的家雀,而是欲搏击四海风云的雄鹰。既为豪侠之士,又值血气方刚之年,故嫉恶如仇,愿铲尽天下不平事,敢作敢为,对贪官恶吏就难免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侠义之举: “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据《汉书·尹赏传》说,长安有一群少年专门谋杀官吏替人报仇,事前设赤、黑、白三色弹丸,探得赤丸杀武吏,黑丸者杀文吏,白丸者处理丧事。这两句写出主人公的孔武有力与打抱不平的侠义精神,令人胸胆为之开张。两句对仗工整,韵律铿锵,有金石声,颇似五律之对仗句式。如果说“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是抑,显得低沉;那么至此则一扬,显得高昂,痛快淋漓。接着又回到今日现实的境界中来: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既然杀公吏、报私仇,触犯刑律,只得避逃海上,并来此边塞之地从军。这其中自然亦有投身疆场,建功封侯的幻想。谁料明珠暗投,他在“此边州”并未能显示身手,展其抱负,其勇武之力与侠义之胆皆不为在上者所重视。他碌碌无为如同凡夫俗子。英雄失路,心绪悲凉。久在异乡为异客,又处此坎坷之境,最易生故乡之思: “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 “辽水”即辽宁省辽河。水“悠悠”亦寓有心思悠悠不尽之意。“复”字下得颇有力,使诗显得音情顿挫。更令人愤恨与羞恼的还不在于个人的荣辱升降,而是胡兵屡犯、主帅无能。“胡兵”原指汉朝时的匈奴军队,此比契丹军队; “汉国”即汉朝,此喻唐朝。“愤”针对胡兵入侵,显得有力,“羞”针对主将昏庸无能,显得深刻。“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两句既是批判社会现实,也寄寓“幽燕客”怀才不遇的弦外之音:倘自己被重用,可“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出塞》),使国家免遭失败的耻辱。诗末借用汉朝李广的典故来写“幽燕客”的不平。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作战骁勇,带兵有方,但他“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后来被迫演出“引刀自刭”的惨剧。“七十战”而“未封侯”,对比何等强烈! 这两句堪称全诗画龙点睛之笔。是诗人“兴寄”之所在。
当时主将武攸宜刚愎自用,又“无将略”,致唐兵大败,震恐不敢进。子昂曾出谋献策,以改变战局,但不被武氏采纳。陈子昂失望悲愤,乃有此“感遇”篇。此诗“词旨幽邃”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四),它不是直抒胸臆,而是借“幽燕客”之“言”批判当时主将之误国,并寄寓自己的悲愤。他曾说: “吾无用矣,进不能以义补国,退不能以道隐身……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 (《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序》) 此诗正是这种诗歌主张的实践。全诗一扫初唐残留的六朝无病呻吟的诗风,有所感而发,故感情沉郁深厚,内容充实有力,富于强烈的现实意义。诗之风格迥异于齐梁与初唐的轻靡绮艳,体现了其“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汉魏风骨”说。▲
陈子昂(公元661~公元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市)人,唐代文学家、诗人,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陈拾遗。陈子昂存诗共100多首,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组诗《感遇》38首,《蓟丘览古》7首和《登幽州台歌》、《登泽州城北楼宴》等。陈子昂与司马承祯、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称为仙宗十友。
 陈子昂
陈子昂 陈曾寿
陈曾寿 陈子龙
陈子龙 萨都剌
萨都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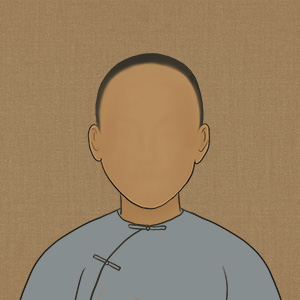 胡秉正
胡秉正 韩愈
韩愈 欧阳修
欧阳修